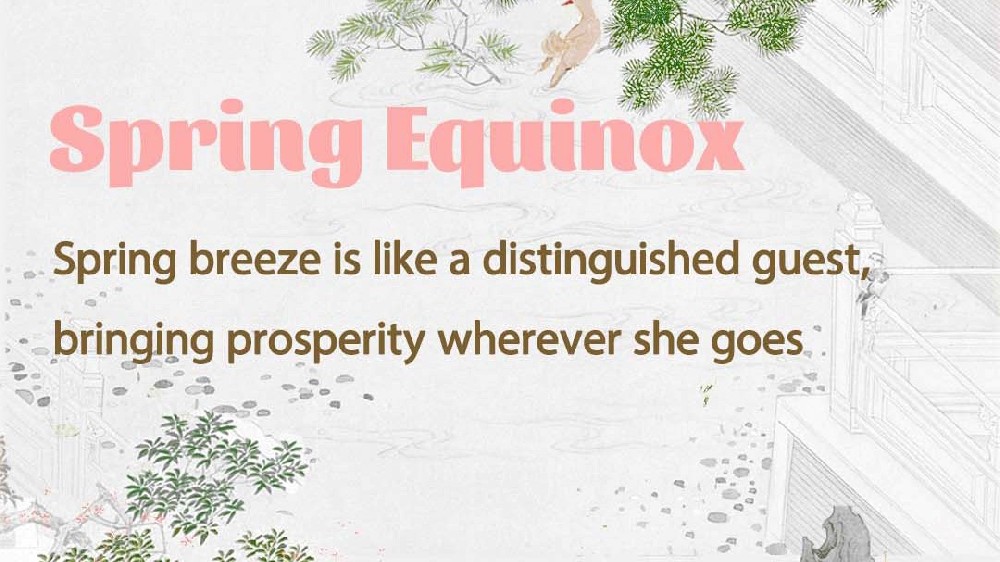原标题为:文明在塌房,一切不过是花招与交易?
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对于“文明”这一主题的讨论再度升温。
在某种程度上,文明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被广泛地用作思想武器,用来攻击一切“他者”与“异类”。为了理解这一切,《毁灭与重生》的作者,牛津大学教授、维纳图书馆当代史奖得主保罗·贝茨(Paul Betts)试图从历史中重新寻找文明概念流传、演变和被扭曲的根源,通过回顾20世纪欧洲历史,挖掘出潜藏其中的思想之战。
毫无疑问,文明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概念,然而这个概念却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欲望、认同感、目标及价值观念。保罗·贝茨坚持对文明进行批判与思考,是因为我们始终处于保卫文明的战斗之中。
理想国此次就这本荣获2021年美国哲学学会雅克·巴赞文化史奖的作品《毁灭与重生》,采访了作者保罗·贝茨。他让我们意识到,在当前民族国家崛起、种族主义抬头、宗教激进化加剧,不同群体间极化与对立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文明或许仍然有可能作为我们在民族国家话语之上进行对话、合作和创造的新方法。
理想国:与您之前的几本书,比如《日常物品的权威》(The Authority of Everyday Objects)、《墙内》(Within Walls)的角度不同,《毁灭与重生》的主题和内容更加宏大,审视了塑造欧洲身份的更广泛的历史和文化力量。您是怎么开始转向这一视角的?
保罗·贝茨:我的前两本书都关注冷战德国的文化层面。《日常物品的权威》一书探讨了大众生产的工业日常用品如何促进西德的经济繁荣和民族认同。《墙内》一书聚焦于实行共产主义的东德,特别关注个人生活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角色和意义。对于《毁灭与重生》,我想扩展其概念和地理范围,重新审视整个欧洲大陆如何在纳粹和“二战”后,围绕着一种针对自身的“再文明化使命”(re-civilizing mission)理念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21世纪欧洲关于身份认同的辩论仍然很激烈,我希望追溯这种身份认同从战后到现在的起源。
理想国:在这本书中,您用“文明”“文明建设”和“文明教化”等许多概念串联起战后的欧洲历史,您为什么认为这些概念如此重要,以至于您可以通过它们来重新解释20世纪欧洲史?
保罗·贝茨:“文明”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它与18世纪的精英主义和19世纪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但让我惊讶的是,1945年之后,许许多多来自西欧和东欧的人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都在使用文明的概念。对我来说,关键问题是:在帝国之后和世界历史上的“欧洲时代”结束之后,欧洲文明意味着什么?我的发现是,1945年之后,关于“文明危机”的辩论思想触及了所有当下的重大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宗教与科学、帝国与反帝制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主义。它是描述和理解战后欧洲及其在世界变化中的地位的主要概念。
奥斯威辛集中营并没有让关于文明的政治语言消亡。相反,文明再次成为一种中心隐喻,赋予战后物质和道德重建以积极的意义。本书以1945年的物质和道德废墟作为清算和机遇的开始。战后,欧洲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历史遗产实验室。
一方面,欧洲的重新文明化直接与和平甚至进步的左翼事业有关,包括和平主义、铁幕下的福利国家政策、反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另一方面,在对文明的呼吁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保守甚至反动的逆流,其中包括对帝国的捍卫、激进基督教、种族主义和对移民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和暴力都是欧洲遗产的一部分。
理想国:在这本书中,您认为文明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人们认为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现实问题,您是否可以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保罗·贝茨:我想展示文明如何从一个抽象的概念演变为一系列务实的改革举措,从而在战后开启新的篇章。
这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对话,而是文明如何成为一套实践,用来重建欧洲和欧洲人。书中的例子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从人道主义、国际司法和军事占领,到去纳粹化政策、大教堂修复,再到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和平运动以及指导人们举止得体、修养自我的社交礼仪书籍的写作。具体来说,比如本书开篇就讲述了1945年的援助工作者,他们是战后废墟中最早的重建者和讲述者。
我还特别关注了新闻记者、礼仪手册作者、文化节参与者等等,许多被遗忘的人为欧洲更广泛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我想恢复他们——作为1945年后欧洲的共同建设者——的那些不被人们看到的贡献。
理想国:本书强调了欧洲文明概念的动态本质,表明其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欧洲文明的叙事发生过怎样的改变?
保罗·贝茨:铁幕两侧和许多前殖民地的人们曾经怀着重建和改革的热忱,参与到文明重建浪潮之中。
参与者形形色色,既有主战派也有和平主义者,既有文物保护者也有自由主义现代化推动者,既有科学家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也有基督教保守派和东欧共产党人,还有欧洲帝国主义者和非洲反帝国主义者。
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文明是单一而普遍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文明是多元而独立的。但所有参与者都认为文明的竞争是紧迫而必要的。
战后欧洲就“文明是什么”以及在纳粹主义、战争和帝国之后文明能成为什么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文明是“被发明的传统”中最珍贵的,在危险和混乱时期,召唤文明的声音往往最为响亮。
这是一个让人们思考欧洲在民族国家、冷战分裂和帝国之外的位置,并基于欧洲过去和现在之间重新绘制出的关系来提出身份政治的常用术语。因此,文明的观念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将集体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嵌入到想象的历史和基于地理范围的身份认同之中。
理想国:这本书止于冷战结束,我们在书中似乎看到和平、多元化的欧洲文明的叙事已经被打破了。在冷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的今天,是否有新的叙事来代替它?
保罗·贝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国际讨论中出现了回归文明概念的趋势。自东欧共产主义和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对于文明处于危机状态的担忧,是衡量国际转型的一个重要指标。
像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ctor Orbán)和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等领导人,以及曾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都经常在他们的政治言论中使用“捍卫文明”作为口号。这种术语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学者——尤其是政治学家——现在开始谈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s)的到来,将其视为文化和权力政治的一种新混合体。
在我们这个时代,右翼势力劫持了文明陷入危机的观念,以此挑战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在18 世纪和19世纪,文明的概念(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始终关乎对人民的改造和进步。它通常伴随着强制和暴力变革,无论是国外的基督教化或西方化,还是国内的阶级斗争。历史上的文明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地;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
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政府则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的国家边界。与先前人们对文明的看法不同,当今保守派对文明的理解——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并不渴望文化交流或相互理解,而是利用基于与他人保持距离的神秘感以及最重要的对被承认的需求来进行交易。
这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发展。这里值得记住的是,文明可能一直与身份政治有关,但最初它被认为是地域性身份的表达,这些身份早于民族国家或超越民族国家。
这具有巨大的讽刺意味,因为将文明理解为重新诠释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的历史单元——这种观点最常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联系在一起——始于拒绝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观。而现在,文明的语言却被用来强化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观。
理想国:您在开头和结尾反复提及伊斯兰国炸毁叙利亚古迹的事件,为何这起事件特别引起您的注意,它本身是否表达出一些特别的含义?
保罗·贝茨:是的,这本书以毁灭为框架,首先是1945年的中欧,然后是最近的叙利亚和其他地方。
我想表明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那个著名的评论,即所有文明的建筑物也同样是野蛮的纪念碑(建立在权力和排斥他者之上),这与20世纪下半叶乃至我们这个时代都相关。
但我也想强调很容易被遗忘的一点,就是与文明相关的许多论述和活动也是和平与进步的运动,而不仅仅是战争和暴力。1945年后欧洲危机故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努力在超越战争、帝国、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好的欧洲。即使有很大一部分失败了,但其中的一些部分确实取得了成功,并且值得我们回忆其全部结果,来帮助理解战后欧洲。
理想国:您为什么特别选择关注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关系,并详细考察殖民主义的遗产和两大洲之间持续存在的联系?
保罗·贝茨:我加入有关非洲的章节,是想观察欧洲文明的概念在欧洲之外,具体来说是殖民时代之后的非洲,会发生什么变化。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的意识形态在为那里的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进行辩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我在书中展示的那样,这是一个始于 19 世纪并持续到20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初期(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故事。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等许多非洲知识分子不断批评欧洲文明是一种带来世界和自身毁灭的暴力意识形态。事实上,塞泽尔谈到了帝国主义如何让欧洲“去文明化”。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许多其他非洲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包括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塞内加尔诗人与政治家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并不想完全抛弃文明的概念。
相反,他们努力根据自己的目的重新塑造它,通常使它与不断发展的非洲文明观念相联系。对于他们来说,非殖民化意味着承认一个由多种平等文明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哪个大陆(尤其是欧洲)享有垄断地位或先进地位。这种去殖民化文明的观念成为后殖民时代到来以及主权的关键表达。
理想国:书中提到,丘吉尔曾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英国脱欧的决定引发了人们对欧洲一体化未来的质疑。您是否认为欧盟能够克服所面临的挑战,并仍然是深度跨国合作的典范?
保罗·贝茨: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实验性的欧洲联邦主义,以及一个致力于和平、法治和自由贸易 (即使不是自由流动) 的跨欧洲文明的梦想。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欧洲一体化的故事一直是成功的,并且在我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如此。英国脱欧后的困境众所周知,它让英国公民和外部观察家都明白,离开欧盟并没有给英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安全或全球影响力。因此,英国的离开反而加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该进程仍然是许多国际观察人士眼中跨国合作的典范。
理想国:本书最后论述了世界重新出现分裂的可能性。最近发生的事件,例如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等事件,凸显了全球稳定的脆弱。面对这些挑战,您如何看待全球和平与合作的前景?
保罗·贝茨: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声音,主张更和平、更包容、更多元文化的欧洲文明或世界文明,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呼吁新的地球文明(planetary civilization)的合作理念,但这些理念正处于危险之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明话语主要被右翼所掌控,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我们需要反思这如何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西方或欧洲价值观的理解的改变。
在西方,保守派政治领导人和一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利用这种言论来使国家建构计划合法化,这些计划以种族、仇外心理和狭隘的民族归属观念为前提。与之相比,桑戈尔和教科文组织等倡导者所提出的开放、融合与包容的多种文明的旧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想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国际政治圈中影响力较小。
自60年代以来,欧洲左翼放弃将文明作为与进步事业相关联的思想,这是关键的思想发展之一。这样做的结果是,文明现在被用来合理化排斥、镇压、加强边境管控和修建隔离墙的行为,这是90年代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负面影响。
在未来,文明将会如何被用来讲述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政治恐惧以及变革,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对文明概念的回归表明了从冷战结束到今天,人们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