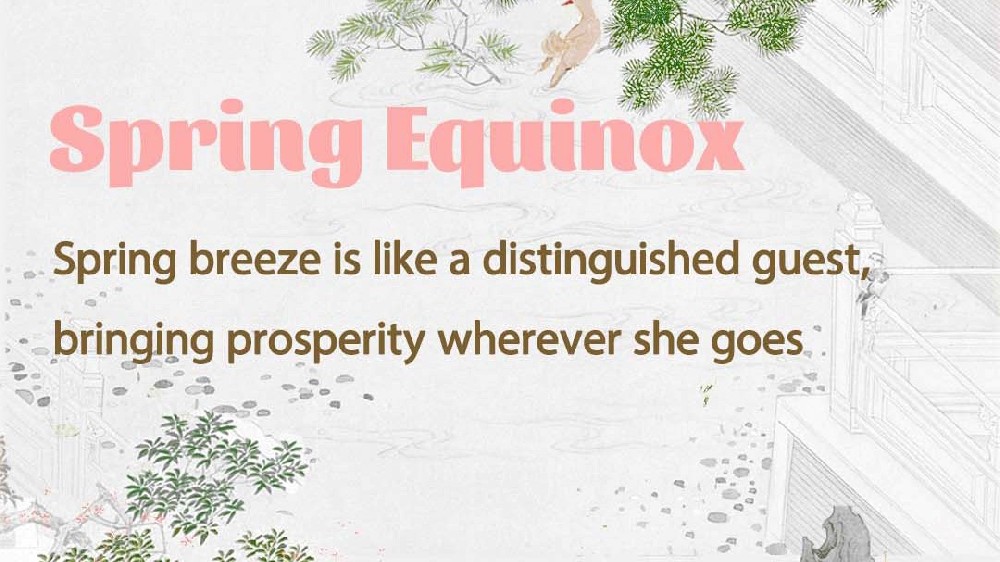在唐代,随着岭南经济与交通的发展与改善,中原社会与岭南的联系日趋紧密。但是,相较于占据中原核心文化区的北方,岭南处于边缘文化区,仍偏于落后,成为大批文人士子的流放地。这些贬谪文人群体非常关心生态环境,他们在诗歌中流露出异于中原创作的“新质”,这种“新质”突出地体现在一系列岭南疾病意象群的创造上。
翻阅《全唐诗》,不难发现大量涉及岭南疾病意象的作品,多以瘴疠、含沙等形态为标志,体现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心理内涵。
瘴疠:艰险生态环境的生命焦虑
岭南地区地域辽阔,全年多雨潮湿。唐代诗人笔下的岭南瘴疠充塞,环境极为险恶。瘴会致病,亦易危及生命,唐代人通过不断地书写“瘴”,来表达处于艰险生态环境中的生命焦虑,使岭南瘴疠意象充满悲情色彩。
在古人认识中,岭南地区瘴气与其气候有关。瘴气之盛,常在夏天暑热时节,危害甚为严重。因此,古代做官者都不愿出仕岭南,唐代人通过诗歌也表达了他们对瘴气的担忧,最典型者当如唐朝大臣、诗人沈佺期。
沈佺期曾流放岭南驩州(今广西崇左市),其诗《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云:“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这里的“岭”指的是大庾岭,常代指岭南。当时,沈佺期同杜审言等人同时获罪,被贬谪岭南,此诗乃沈佺期为杜审言所作。诗中所写岭南之远阔、白云之飘浮、崇山之瘴疠等地理景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无限感伤。作者有意味地延伸了岭南与中原空间之距离、时间之悠长,充分流露出其羁旅怀乡的不舍与愤懑之情。沈佺期诗再如“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疟瘴因兹苦,穷愁益复迷”“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鬼门应苦夜,瘴浦不宜秋”……皆烘托出岭南驩州恶劣荒僻的自然地理环境。无论是“不堪闻”“满冬秋”的瘴疠(特指),还是云雾缭绕、毒瘴熏蒸的瘴江、瘴浦(泛指),皆表达了诗人无辜受冤流放岭南身心所受的痛苦折磨。沈佺期离开京师后,日渐衰老,或许就有岭南之瘴的影响。
据统计,唐代仅贬流广东有史籍可考的左降官有200余人。这些名士,从高高庙堂坠落到瘴乡蛮地,从权倾一时到罪责在身,瘴疠于是由一个地理疾病概念上升至诗人寄托生命忧虑的情感意象。
因此,将岭南视为远在天涯海角、对岭南瘴疠惶惶不安的思维模式,在唐代以“南贬寄赠纪游”为主题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李明远的“北鸟飞不到,南人谁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宋之问的“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张均的“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以及李德裕的“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等诗句,皆反映了他们对岭南炎瘴环境的焦虑心态。远谪岭南生涯,饱受瘴气愁苦,使文人有悲凄之感。
唐代诗人极言“瘴”,还常常把岭南的山、川、云、雾、烟、树都与之相联系,“瘴烟”“瘴海”“瘴云”“瘴山”“瘴雾”……诗人所述之“瘴”,实际不再是单纯的时空符号,同时也是渲染之辞,反衬出诗人人生沉沦的忧怨心境和孤独处境。
在这个意义上,“瘴疠”明指岭南的炎荒万里、毒瘴充塞的自然环境,暗指贬谪岭南士人的失意人生,是诗人生命的流衍、情感的表征。
含沙:迁谪悲凉身份的心理投影
含沙,又称蜮、射工、短狐等。传说其能在水中含沙射影,使人致病,故称“含沙”。《本草纲目》虫部第42卷记载其为“溪鬼虫”的别名,《诸病源候论》卷25记载,含沙主要生活于水中:“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因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入人家,或遇道上牛马等迹内即停住,其含沙射人影便病。”有学者提出,含沙类似今天的恙虫病,即由恙虫立克次体所引起的急性发热性斑疹寒状传染病。唐代诗人在流放途中,耳闻含沙毒害,在迁谪屈辱悲凉的心境下,其笔下的含沙意象充满着悲惧之感。
唐代岭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一地区植被丰茂、环境潮湿,适合含沙等危险物的生存。在掺杂着悲伤与忧惧的巨大心理压力之下,唐人势必会对含沙形成一种深重的心理,其畏惧惆怅之情油然而生,最具代表者当如宋之问。宋之问曾两度被贬官岭南,在岭南留下了大量传世名篇。最出名的就是《早发大庾岭》,其诗曰:“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含沙缘涧聚,吻草依林植。适蛮悲疾首,怀巩泪沾臆。”诗中点出当时情境:被贬出京,背井离乡,眼见就要由中原昌明之腹地到瘴房含沙之蛮荒去受煎熬,一阵离乡辞朝的痛苦袭上心头。途程的艰险与遥远难以预料,如今登上崇岭更觉怅恨。这时,自思自忖,想到获罪遭贬地区环境恶劣、含沙弥漫,不适宜人生存,既悲且怨。全诗风格凄切哀婉,眼前的“含沙”自然景象也便有了沉痛的感情色彩。
根据《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诗人粗略统计,唐代岭南诗人约260余人,除岭南籍作者30余人之外,其余全是南迁岭南作者。唐代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李峤、崔融、张九龄、王昌龄、李绅、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德裕等都曾遭南贬。对于这些文人而言,他们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其理想抱负更加难以实现,又时刻面临着含沙疾病威胁。就含沙的传播媒介恙螨而言,它主要孽生于阴暗、潮湿的丛林边缘,或者溪沟、江河沿岸的灌木杂草丛中。所以,来到岭南的文人,对水边含沙的书写就不足为怪了。如张祜诗曰“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刘禹锡诗曰“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可以看出,在时人看来,前往岭南一定要小心含沙。
可以说,僻塞艰险的岭南生态,对南迁中原人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含沙意象的反复运用,乃是诗人贬居岭南极度低落心情的真实写照。而乡思客愁、政治追求、生命价值,就成为了唐代岭南含沙意象烘托的主旋律。
唐代南迁文人的作品构成了岭南诗歌的主体,这些文人与岭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相作用,使唐人岭南诗歌在意象的特征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异变,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以瘴疠、含沙为主的岭南诗歌意象群落。这两种意象在袁不约《送人至岭南》一诗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瘴烟迷月色,巴路傍溪声。畏药将银试,防蛟避水行。”
文人不断通过对岭南文化元素和疾病意象的摹写,以此来构筑其心灵深处的形式,表达他们内心的苦闷。这一意象群承载着诗学精神与审美抒写,是诗人生命荒废感的时空思维与艺术表征。
作者:谢文惠
编辑:张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