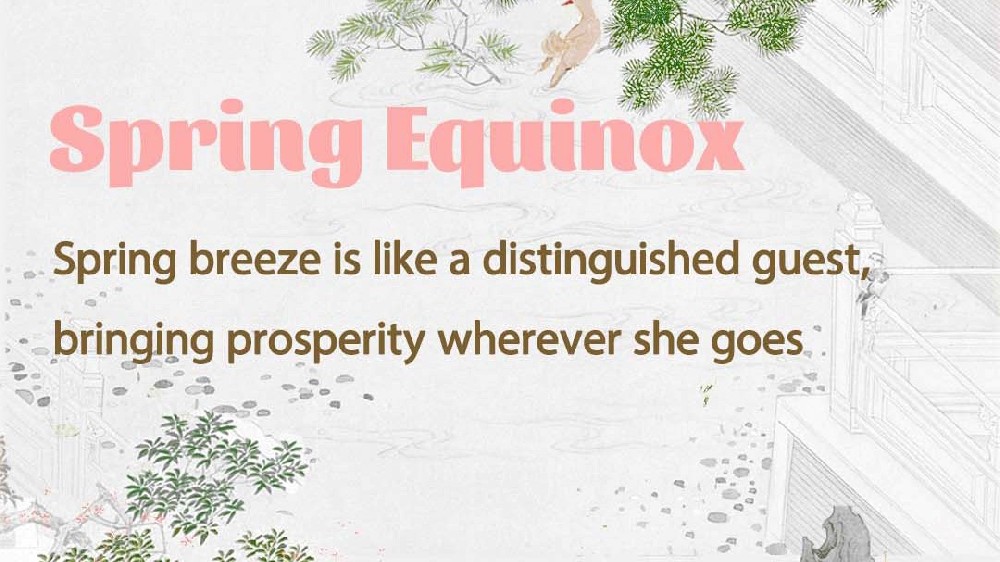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要求我们要以中华文化立场阐述好、传播好中华文明。但是,长期以来,在对外阐述和传播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存在着方法和目的相混淆或者过于简单化的问题,致使很多时候传播效果未能达到预期。
例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是一种出发点,也是一种内在的原则和方法,但很多时候被简单地外化了,这就显得比较生硬。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一内在的原则、方法本身作为目的,以与之未必直接一致的外在方法更好地实现它——当然,这种外在的方法本身也应该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在理论阐述和传播中,以何者为目的、以何者为方法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决定着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气象和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学者竹内好、沟口雄三关于“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讨论被激活为当今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追溯起来,这一范式是针对“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而提出的。
所谓“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正如沟口雄三指出的,就是近代以来日本和西方在研究中国时,“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但是,“这样的‘世界’归根结底就是欧洲”。英国学者维克托·基尔南有本书的标题就叫“人类的主人——欧洲帝国时期对其他文化的态度”。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汉学(Sinology),还有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学(Orientalism),虽然对发掘文明、传播文化有重要贡献,但存在着本质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开眼看世界”“面向世界”的先进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视为了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度把追赶西方和融入世界看成一回事,“全盘西方”的思潮一度流行。
这样就达成某种世界历史的“合谋”:西方就是世界,是中国、非西方的标准和方法。直到今天也不乏此类例证,例如2022年爆出的教材插图事件和某高校创作“眯眯眼”体现国际美等事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当今我们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理由。
作为以世界为方法的对冲,所谓“以中国为方法”,正如中国学者汪晖指出的,是要求将中国“转化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即将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关系置于政治分析的棋局之中,进而产生出政治性的召唤。其中酝酿着一种强烈的普遍性关怀。”也就是说,以谁为方法就意味着以谁为主体或使谁成为主体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继本土的东方学(萨义德所述的东方学的“东方”并不包括中国)之后兴起过关于中华性(Chineseness)的讨论,强调自觉与西方现代性相区分,这是学术上自觉的“以中国为方法”。当下不少关于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现代性模式、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研究也蕴含着这样的旨趣。包括我们讲的阐述和传播中华文明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也是如此。
无疑,“以中国为方法”的主体性凸显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在对外阐释和传播中面临着相互关联的两方面问题:一是以中国为方法如何和一般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二是中国的“普遍性关怀”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指责。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中国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都贯穿着“人类”的逻辑,都在应答人类的时代之问、命运之问,是以人类为目的的。
以人类为目的事实上凸显了民族国家、个人的主体地位,与那些不以人类为目的而只是本能地以自己为目的的狭隘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当今时代人们更需要自觉地以人类为方法。中国的一系列主张中本就蕴含着这样的理解,或者说只有这样理解这些主张才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而不能仅仅将之理解为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人类为目的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对外阐释和传播中也是如此。
1.以人类为方法意味着一种人类整体的视野和情怀,要坚持胸怀天下。
以人类为方法,首先意味着承认群体、个体的差异性存在是既定的事实,也意味着在承认、尊重差异的同时使自己相对化,而不是高人一等。中国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始终强调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因此,我们在对外阐释和传播过程中,要力避把差异说成优越、把多元性的方案之一说成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们为世界提供的是中国方案,方案总是意味着有多种。
2.以人类为方法意味着一种人类共同主体的自觉,要凸显全人类团结。
以人类为方法意味着除开个体、民族国家等群体外,要以人类为主体,自觉建构人类层面的主体。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超越以“市民”社会为立脚点的旧唯物主义,而代之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立脚点的新唯物主义。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作为共同主体的意识,需要共同的意志去完成共同的任务,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延续共同的生命,这正是主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我们学习二十大报告都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感受,那就是报告特别强调“团结奋斗”。这不仅对于当今中国自身来说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来讲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团结奋斗,就是要凝聚为共同体去做共同的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如此。这也启示我们,在对外阐述和传播中要更自觉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更多突出“我们”而不是“我”,更多讲好共通、共同、共享、团结的人类故事。
3.以人类为方法意味着一种人类原则高度的规范,要注重反思学习。
方法既是手段、途径,也是标准。以人类为方法就意味着从人类的角度“凝视”民族、国家、个人,形成其行动合理性、合法性的根据。老子曾说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当我们将“天下”作为方法时,不仅需要以天下观天下,而且需要以天下观邦,以天下观乡,以天下观家,以天下观身——或者说这本来就是“以天下观天下”的题中之义。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在人类既有文明形态中增加一个成员,而应该理解为这种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以人类为方法、原则基础上的,吸收了全人类现代文明积极成果。唯此,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类”的“新”的文明形态。在对外阐述和传播中不能光讲自己的好,要讲我们学习了别人的好;因为学习借鉴了别人的好,得到别人的帮助,才变得更好。
4.以人类为方法意味着一种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叙事方法,要突出当地的主体地位。
以人类为方法就要借助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比如说行动者取向的主位观点:不是要回答从研究者的角度应该如何看待被研究者的行为,而是要从作为被研究者的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感受,关注他们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所作所为及其所在的生活世界。“他们如何感知与分类这个世界?他们用来解释行为的规则是什么?对他们而言,什么东西具有意义?他们如何想象与解释各种事物?”(科塔克:《文化人类学:领会文化多样性》)。这就启示我们,在对外阐释和传播中华文明时,要真正站在所在国家、民族大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而不是代替他们思考问题;要了解他们所思所想所需,尽量避免想当然的主观主义错误,更多以各民族、国家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尤其要团结那些长期处于西方主导话语边缘的国家、民族,帮助他们提升话语权,深信他们的自我澄明在最深层一定是与我们共鸣乃至一致的。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贯穿着“人类”逻辑,是“以天下观天下”的智慧结晶,是既以人类为目的又以人类为方法的行动方案,其中蕴含着对我们阐述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方法论启示。
增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应该简单理解为增强民族性及一般的对人类性的贡献,而要自觉加强基于人类性对民族性的提升,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统一。或者说,在当今时代,以中国为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最高境界恰恰要自觉地以人类为方法。以此为遵循,我们的对外阐述和传播才能更加有效。
(本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沈湘平在“中国文明观话语体系建构原则与基本思路”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编辑时有删改。)
本期编辑:肖可心